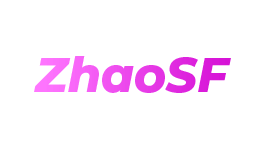
往北走
宅在家里足不出户,吃饭睡觉看书写字,是我这几年最满意的日子。这周日,难悖同学老苏几次盛情相邀,北走了一回。下午七点动身,到达延安还不到九点,苏才从菜地里回来,扑闪着车尾灯在路边接我们,见面先是责备,怎
宅在家里足不出户,吃饭睡觉看书写字,是我这几年最满意的日子。这周日,难悖同学老苏几次盛情相邀,北走了一回。下午七点动身,到达延安还不到九点,苏才从菜地里回来,扑闪着车尾灯在路边接我们,见面先是责备,怎么不早打招呼,让他一身腌臜见人。他说领我们去吃羊肉面——晚上九点,他想安排两个女士咥一老碗羊肉面!我和女友面面相觑,太爆太重口味了吧,快睡的时候,撑一肚子高热量的碳水化合物,外加膻腥浓腻的羊肉,这一晚上可怎么睡?明早一准上火,变成两眼发红的兔子妈,何况女友本就忙碌上火嘴唇气泡了。厚着脸皮请他调整,照顾一下女士的餐饮习惯,原则是越简单越好,越清淡越好,最好一点薄粥,一碟儿小菜。还好酒店没有拒绝我们的低消费。陕北小米本来就黏香,煮了绿菜在里头,悦目爽口,咸菜丝儿、黄瓜片也都可心。
早上五点起床,按头天晚上说好的时间洗漱完毕,在浓睡未尽中坐等老苏。六点一刻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北往山西而去。过清涧,从车窗往外打量这个被誉为红枣之乡、道情之乡、石板之乡、粉条之乡的独特之处,很遗憾,中国的城市都是一个样。大清早,我看不到街市的红枣,听不到高亢的陕北道情,也没有发现我酷爱的洋芋粉条。在延安上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实际上一路走来,用于建筑的石板一块也没看见。若要硬要找些不同,那就是清涧街上林林总总的饭铺多曰煎饼铺、煎饼店、煎饼宴,找到头,还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卖煎饼。当作主打的东西总有它的好吧,那就吃煎饼。我由此钦佩了清涧人民无比强韧胃肠。雪白的荞面煎饼是凉的,佐餐的每人一碗泔水样的酸汤也是凉的,煎饼里卷的豆腐干、洋芋丝、肉丝,全是凉的。蘸着温凉的番茄汤吃,我边吃边胆怯,这一肚子冰凉,尤其是冰凉的肉丝,再加上七拐八拐颠簸的道路,肯定晕车。果不其然,未到山西,我的肚子里开始小规模的叽里咕噜闹腾,好不容易挨到一处加油站,急急奔去处理。这么一泻,人轻松了,疲倦又来,汽油味、车内空气不流动的人体味,车子起步刹车减速都让我天旋地转嘴里发苦,可能是胆汁倒流了,话不能说,水不敢喝。也怪不得一顿凉煎饼,是自己的肠胃不争气罢了。
晃到平遥足足用了六个小时,就近找了一家餐馆午餐,点了他们的特色菜:莜面“栲栳恅”和烂糊白菜。栲栳恅算是美味,那个烂白菜也名副其实——是名副其实的胡整,它是这样的构成:稠乎乎的汤里乱七八糟的煮了娃娃菜、荷包蛋、香肠,还有其他什么碎碎的东西认不出来。老苏将菜拉到他和司机老陈面前说:咱们吃吧,你看她俩的表情,估计不会吃。刚吃一口,老苏就大喝一声:服务员,拿盐来!第二天在绵山脚下农家乐,老苏终于不忍了:你蒙山西人咋跌?昨天那家不放盐,今天的厨师是不是延大函授毕业的?店家愣了,我们也不解,想了一会才明白,延大是“盐大”,函授即“咸受”。(陕西方言,咸读寒音。)他的发明还不止于此:饭前把筷子扎进蒜里擦拭消毒。我们学到了一手,并将其广为宣传。
五、六年前来过平遥,当时将包忘在车里,兜里装了10块钱,好多眼花缭乱的精致玩意都没买成,一直念念不忘。女友也来过,她目的明确,只惦记那些手工做的千层底绣花拖鞋。苏买了一瓶五斤装的杏花酒。他这人,一辈子爱书爱酒,血压高发誓戒酒的,他说拿回去放在柜子上看。哄鬼呢。
故地重游,渴望减了七分,那些工艺品也不再诱人,满地摊儿都有。老城建筑也与其他中国古建筑无异,红砖碧瓦翘尖尖。而且,它本就是七十年代水毁之后的复制品,没甚历史。人说夫妻是第一碗饭好吃,景致也是。没有新鲜感,也就没有兴致,没有精神。二返平遥,倦倦的走了三个小时,几乎找不到迫切记录的东西,笔攥在手里,纸忘了拿。人生,经历多了,激情就磨砺少了,那些曾经悦目的东西如今看起来都平平常常,风韵不再,甚至满眼艳俗之气。生活中,繁复的东西实太多了,像苏格拉底说的:有这么多我用不着的东西啊。生活被谁弄的如此复杂呢?
平遥八十四条街,看了不足二十,几个大钱庄都懒得去,更淡的,是连门票都没买,租了辆电瓶车围城咣当了一圈,司机再三劝说找个导游,我扬扬手里两块钱买来的景区介绍,懒得跟他多说。
绵山也去过,但因为当年挑的日子不对,恰逢五一黄金周,车堵在壁立的山腰险径,前不得前后不得后,挨到半山,天已黑透,好歹没一块睡处,只得下山,山里头的景致其实没看到,倒是领略了悬崖峭壁之上壮观的人造景观,尤其是那个“之”字形的天梯,仿佛一幅遥远的写意画,云天之间,谁在暗灰的纸上,比着尺子淡淡的画了几个相连的直线,人像蝼蚁一样,沿着那线往上爬,爬过骇然壁立的悬崖,或许就通了南天门,通了王母的瑶池。
庙宇塔楼赫然建在山顶,须仰视才见,恍若贸然涉足另外一个神秘世界。
绵山景点增加很多,设施也较前便捷,理所当然的多了些限制,比如,除了景区的大巴和在山里住宿的车辆之外,其他车再不准上,我们试图冒充上山住宿,人家当然比我们聪明,要出示住宿单。山上一晚五六百块前,无论如何不当这个冤大头。
为了一晚住宿,两个拉客的女人争执不下,一个说早就占下了我们,另一个说谁占下也不顶用,关键看客人想到谁家。结果,我们随那声量气势弱的女人去她家住,并非故意回击那个凶煞村妇,我们不想将自己关进任何一家酒店房门。坐在农家小院,仰看绵山巍峨,凉风习习,品尝地道的农家菜,是出行千里万里都不倦的心念。而且,其他三个同伴还另有收获,卧听邻居半夜打架。我什么也没听到,睡的跟死了一般。
赏绵山,我有两个惊讶,一是惊讶晋商的胆识。焦炭大王阎吉英,本是个农民,充其量是沾了改革开放初期商机的暴发户,但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斥巨资开发绵山旅游,不可谓不是胆识过人与众不同。那时,各地都在喊旅游兴省兴县,但民间投资的绝对是凤毛麟角,副人烧钱、拿钱打水漂都不稀罕,但拿十亿身家砸,这一砸,可比绵山的险险的多,不提心吊胆才怪?信不信人各有命,命运总是格外关照那些胆略过人的人,姓阎的成功了,据说成本早已收回,余下的,就是数钱和不甘寂寞再度冒险了。
第二个惊讶,是万丈壁仞之上的工程建设。前面说过,绵山的公路、涵洞、栈道、庙宇、楼阁,
版权声明:本文由zhaosf新开传奇网站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