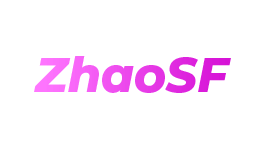
构筑理想国
查尔斯·兰姆终身未娶,当别人向他夸耀自己的孩子多么有出息的时候,他愤而发表《一个单身汉对于已婚男女言行无状之哀诉》的文章,声称孩子没有什么稀奇,跟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到处都有,没必要在他面前炫耀。无论他的
查尔斯·兰姆终身未娶,当别人向他夸耀自己的孩子多么有出息的时候,他愤而发表《一个单身汉对于已婚男女言行无状之哀诉》的文章,声称孩子没有什么稀奇,跟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到处都有,没必要在他面前炫耀。无论他的话是否中肯,也无论他骨子里怎样的葡萄酸,每位家长都竭尽所能培养子女,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并且远远优异于别家的孩子。中国不缺教育,古往今来,思想灌输,道德陶铸,层出不穷。对子女的教育尤甚,历朝历代,家书、家训浩如烟海,不济如孟母者,也懂得择邻处的意义,孟母三迁非图居住的舒适。现在的教育早已变味,该崇高的时候虚妄,该现实的时候媚俗,小学生类似于成人竞争,大学生却学讲究卫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空洞的励志图书横行肆虐,高居书店要位,青少年趋之若鹜,不加选择地效仿。少不更事的青少年固然需要榜样,需要喝点心灵鸡汤以滋补,可是有汤无鸡肉的励志图书,并无些许裨益。
空洞的励志,不独是现代人的弊病,古人对此也呵詈万端。颜之推作《颜氏家训》,开篇就大加挞伐——“魏、晋已来,所着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先进的观念,说“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希望通过自己言之有物的文字,给予较傅婢寡妻更大助益的教导。
黄长营的《过洞庭》,是一本以自己亲身经历写就的励志书籍,有汤有鸡肉,营养滋补,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一样,能够给予较傅婢寡妻更大助益的教导。作为父亲,黄长营恨不得将知青时候的每一个细节都再现在女儿面前,以期女儿在遇到人生挫折的时候,能够鼓起勇气直面应对;作为写作者,黄长营以自己为基础,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不屈不饶的精神描摹得恰如其分,长者能够从中窥出自己当年的影子,少者除了了解那段特殊历史之外,还能够萌生出对工作或者生活自强不息的意志。
中国的史书有两种,一种是通史,一种是断代史。可是文革那段历史缺无,通史、断代史一跳而过,成为名副其实的“断代史”,鲜有人知晓。记得中学学过近现代史后,有一次非常困惑地问曾是知青的老爸,我说你老人家就那段历史整天诉苦,可是史无明志啊,莫非你在编故事吓唬我。老爸重重地敲我一脑勺,愤恨难平地叫骂,你个兔崽子,历史不写,难道我当年捡茅坑上的饭粒吃是白捡的!
饭粒没白捡,老爸借以活过命来,并在往后的路上一步步走得很高很远。不过,相较于《过洞庭》的作者,老爸还是逊色得多,一辈子对茅坑上的那颗饭粒念念不忘,每次听他念叨,我总会条件反射地幻想一幕场景:上边吃下边拉,恶心至极。后来看了伤痕文学作品,得知知青不仅饥饿,还做苦力,性苦闷,精神扭曲,一直到现在,伤痕难消。幸而老爸只知道饥饿,一旦意识到心灵被扭曲了,可能就此丧失活下去的勇气。
其实上世纪整个六十年代,全世界都在轰轰烈烈地搞运动,美国有胡士托、嬉皮运动,法国效仿中国兴起红卫兵运动,女人搞女权运动,同性恋搞同性恋运动。旧传统在尼采呐喊“一切价值重估”近百年之后得以颠覆,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潮起水涌,权威可以打到,障碍可以逾越。青年着奇装异服,男女不设防,酗酒嗑药,听披头士音乐,纵情交媾。这是时代构筑的理想国,中国人民提前进入理想社会,外国人民紧随其后。
可是,任何主义、任何理想的构筑,都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嬉皮士被扣上一顶“垮掉一代”的帽子,跟咱们的八零后以及九零后一样,全然成就不了社会的中流砥柱,事实上,后来嬉皮精神在现实面前垮掉了。文革结束后,知青们重返城市,进入各行各业,内心一直郁郁不平,因此伤痕文学兴起。倘若老爸的记忆力能够延伸到茅坑上的那颗饭粒之外的话,我敢肯定,老爸会是一位很出色的伤痕文学作家,可惜他老人家不争气。
《西西里岛美丽传说》结尾处有句非常经典的话,说“回归故里,才能找回失去的尊严。”当我们回忆过往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找回失去的尊严,因此我们会露出甜甜一笑,过去的事情,一经记忆演绎,总是美好的。作者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已然找回失去的尊严,那些点点滴滴幻化成一面镜子,无论是其女儿,还是在读者看来,镜中的影像隐隐的有人格之美。一如托马斯?哈代照镜子时写的诗句那样美妙,“当我照我的镜/见我形容憔悴/我说但愿上天让我的心/也像这样凋萎/那时人心对我变冷/我再也不忧戚/我将能孤独而平静/等待永久的安息/可叹时间偷走一半/却让一半留存/被时间摇撼的黄昏之躯中/搏动着正午的心。”
每个人都应该构筑自己的理想国,哪怕艰险重重。这是本书作者传递给读者的最大信号。一个人可以深陷困境,遭受天灾人祸,而向上的精神不可泯灭,梅花之香源于苦寒。盖?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一书中讲了一个故事,直白却发人深省。一天,一个人在路上走,遇见一个人在打石头,就问他,你在做什么?石匠回答说,我在打石头。走了一会儿,又遇见一个石匠,又问他在做什么?这个石匠回答说,我在作地基。不久又遇见第三个石匠,问了同样的问题。不料这名石匠说,我在建造一座大教堂。《过洞庭》跟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同一的,每个人其实都在打石头,劳累疲倦相随,是否只是打一个石头,还是作一个地基,抑或建一座大教堂,看过《过洞庭》就有答案。
版权声明:本文由zhaosf新开传奇网站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