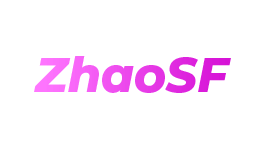
与那个老人的梦境湘西曾有约会
身为黔地山民,对东面邻省湖南的山光水色人文风情自然是浮光掠影地知道一些,但对那些普天之下相同而少有个性的亭台楼阁或鳞鳞大厦,同样提不起太多的兴趣。中学时代便知道了一个叫做桃花源的胜境,据说就在湖南的武
身为黔地山民,对东面邻省湖南的山光水色人文风情自然是浮光掠影地知道一些,但对那些普天之下相同而少有个性的亭台楼阁或鳞鳞大厦,同样提不起太多的兴趣。中学时代便知道了一个叫做桃花源的胜境,据说就在湖南的武陵,但那个胜境,是陶渊明的;生长在乡野且对乱世毫无感性认识的我们,历来就觉得它平常不过,不具备任何神秘感和吸引力,自始至终没有动过身往或神往的雅兴。中学毕业不久,无意中从资料上知道了一个出生于湘西、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说算是特立独行的名叫沈从文的老先生,知道了他在二十世纪初到北平谋发展的一些既辛酸、有时却又让人觉得有趣的经历,还大略地知道了他的作品,知道了他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岑寂与磨难,知道了他去世后与诺奖失之交臂的“佳话”。
接触老先生的《边城》,先是在中文专业的现代文学教材里,属于梗概性质的“压缩”品,读了,觉得意犹未尽。读完这门功课之后,特地买了先生的一些作品,包括《边城》的一个单行本。仔细展读,才觉得当初“压缩”品的作者,还是基本上抓住了故事主线、没有遗漏的。先生的《边城》,包括后来创作的《长河》,都各像一部以刻画梦境湘西为主题的悠长散文。前者像是一部长篇抒情散文,后者,则更像是几个短篇叙事散文作品的合集。
认真看完小说《边城》之后,萦回于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的那一份怅惋之情,让我逐渐明白它的引人之处,其实不在于故事,而在于那个源于湘西的凄美梦境,在于梦境中人性的真、人性的善和人性的美,在于主人公“这个人”踪迹未确之时故事的戛然而止,在于读者如我辈对主人公翠翠命运走向的无边遐想,……。后来,每读完一次,我都会“陷进”梦境里很长时间,欲罢不能。
从《边城》、《长河》两部作品还可以看得出来的,是它们与沈从文老先生在解放后困窘遭际的因果相因:在连草莽英雄都要投身革命洪流的那个动荡时代,作为一名具有文化修养又加入过军队的知识青年,离开行伍之后却“置身事外”,“忽视”残酷的社会现实,在笔底营造了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的世外桃源,不被革命者所不屑所排斥才是怪事!
事实上,这是后来者对沈老先生极大的误会,或者可以说是“冤枉”。在发表于1934年4月的《边城》题记中,他开篇便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这与沈老先生一家三代列身军籍有关。“照目前风气来说,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作者对自己的故土乡亲有着真诚的挚爱,对自己的作品所面临的遭遇有着鲜明的态度,而对于时局,对于民族的苦难,作者也决不像后来者所感觉到的那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纵然混乱,时代也在朝前;即使黯淡,历史仍要嬗变,从几年后出版的小说《长河》中,我们已经找不到《边城》中那样的人性美了。诚如老先生在《长河》的题记中所感慨的:“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在这个题记中,老先生对过去淳朴民风的惋惜,对未来创作目标的追求,也都作了直接的坦陈:“《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遗憾的是,即使是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作者的这部与“革命”无关的作品,也依然是命途多舛,得不到发表,屡屡遭禁遭删
时过境迁,当许多革命作品或政治作品被人们遗弃到历史某个角落的时候,老先生的作品,终于被一些人慧眼所识,拂去那厚厚的尘埃,让它超越阶级,甚至跨越时空,重新绽放出夺目的异彩。
两年前的某个夏日,几个人一起闲聊时言及沈老先生、言及湘西的凤凰,一位与我交往不错的女性朋友邀约大家前去观光,说是沈老先生的故乡早已经开发,成为游览胜地了。出于对先生的敬仰,与对那一片神秘土地的向往,我立即欣然附和。可惜约好的日子,当时的应诺者,纷纷都称忙于自己的事务,最后只剩下我与邀约者。二人未便成行,我们却没说放弃,只是无限期地推迟了。
日前再读《长河》,注意到题记第一段中有这样几句话:“‘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接下来对湘西时髦青年的描述,尽管是六十年前的状态,或许仍是六十多年后黔地一些乡野的人们生存状态所不可比拟的。加上最近三十来年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影响,湘西当地各色人等的时髦劲头,怕是更加的超前了吧!
沈老先生着意构筑的那个美好的梦境湘西,也许只能蜷缩于他的作品中,供热爱先生的人们神游罢了。无限期推迟的湘西之约,或者说预期中的湘西之行,大概也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失去兑现的意义与必要了。
版权声明:本文由zhaosf新开传奇网站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